中国文学发展之我所见
中国文学发展之我所见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(19世纪至20世纪) ,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,这种“大河改道”式的转折,决定了中国20世纪文论的基本样态与格局,这种状态几乎持续了近百年。然而,在这
中国文学发展之我所见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(19世纪至20世纪) ,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 折,这种“大河改道”式的转折,决定了中国20世纪文论的基本样态与格局,这种 状态几乎持续了近百年。然而,在这一个世纪之交(20世纪至21世纪) ,中国文 学理论似乎又在开启着另一个转折点,这个转折甚至已经初露端倪,它将何去何 从,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。本文拟通过这两次转折的对比,从经验与教训 历史 中来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的转折与建构。 上一个世纪之交,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之下,开始了“大河改道”式 的巨大转折。这次转折的基本特征是在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中“别求新声于异 邦”,是真心虔诚地向西方,是“拿来主义”。 学习 于是乎,西方的文学理论开始被大规模引进,在短短一二十年间,中国文学理 论几乎是“换了一个人间”。传统中国文论从主流位置退却下来,西方文论大行 其道。由于这一次“拿来”是整个文论话语、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,“拿来主义” 本来的好意因而走了样,拿来的东西淹没了自己,结果“拿来主义”变了味,基本 上蜕变为“取代主义”或“套用主义”。在西方文论的巨大冲击下,中国文学理 论完成了世纪之交的巨大转折,走向了“以西代中”,即以西方文论取代中国固有 传统文论的百年历程。本来,这一转折之初有着多种可能和选择,至少有两种较为 明显的走向:其一是以西方文论来充实中国传统文论,使之在融会中西的过程中 实现转型和产生质的飞跃,在这一历史的“通变”中迈上一个新台阶;其二是 现代 以西方文论来取代中国传统文论,全盘西方化,用西方“”而“系统”的文学 科学 理论,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,并指导现实创作,使中国文学理论在西化过程中实现 现代转化。 这两种走向,在世纪之交的大转折之时都是存在着的。在一些著名学者和文 化人身上, 表现得尤为明显。青年鲁迅的《摩罗诗力说》,运用传统的话语言说 方式,论述了西方“立意在反抗,指归在动作”的摩罗诗人及其精神。该文以“神 思”论文学,以文言作表述。这是一篇典型的以中国话语方式来言说西方文艺精 神的论文,成为鲁迅文艺论著的代表之作。 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,运用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的言说方式,融入了西方文 论概念,如“有造境,有写境,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,因大 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,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”,“宏壮”、“优美”等 自然 美学范畴。这种以中国文论话语言说方式写就的《人间词话》,获得了巨大的理 论成功。薄薄一本《人间词话》,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的典范之著,在20世 纪海内外学界都产生了巨大。 影响 这种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方式融会西方文论的学术路径,即便在西方文论全 面登陆中国之后,也仍然有着极少数的成功个案,顽强地生存着。在著名学人中, 除鲁迅、王国维外,尚有朱光潜、宗白华、钱钟书等人也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采 用了中国文论话语的言说方式。尤其是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,更是 以传统话语方式谈艺说文。《谈艺录》连书名都与明人徐祯卿的《谈艺录》相同, 完全是传统诗话词话的言说方式。《管锥编》则是用中国传统注疏、传、笺的言 说方式,甚至坚持用文言文表述,融古今中外的大量材料为一炉,取得了巨大的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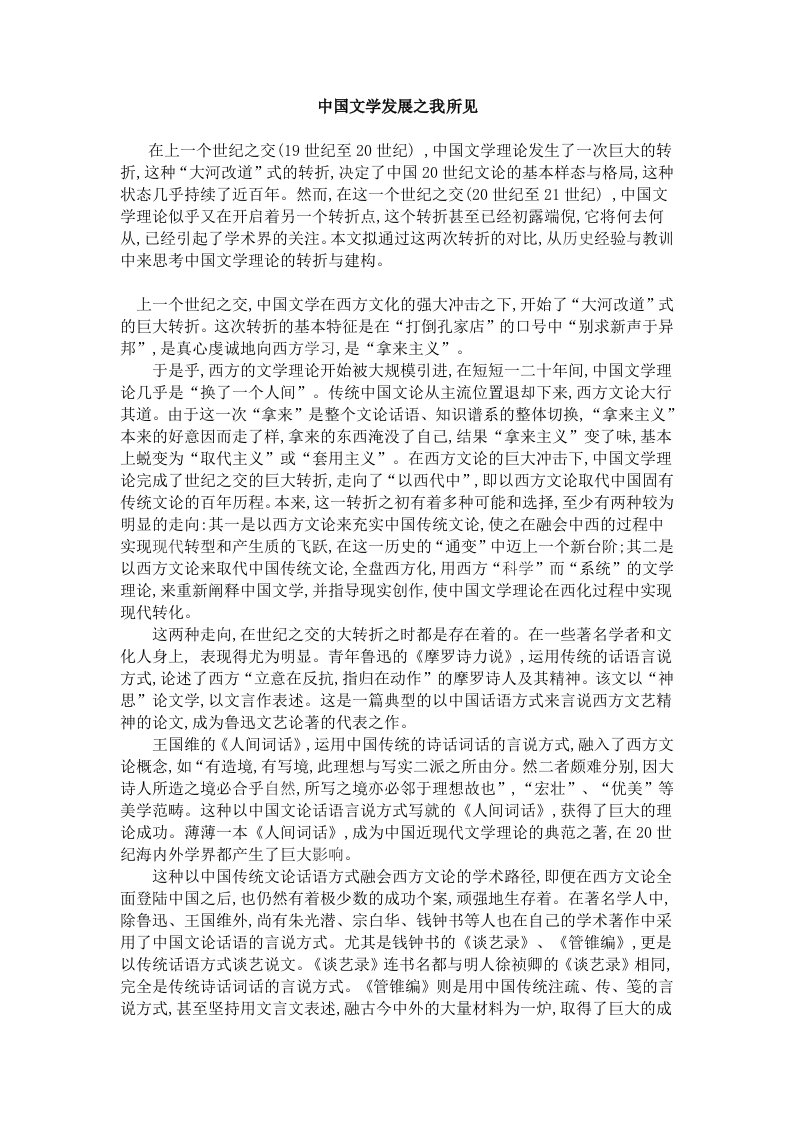
 Word转PDF
Word转PDF